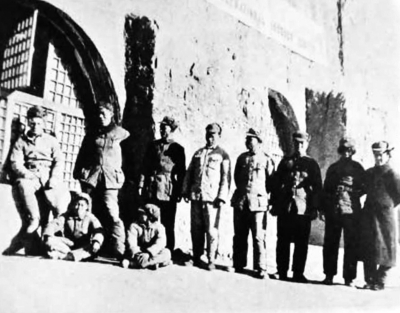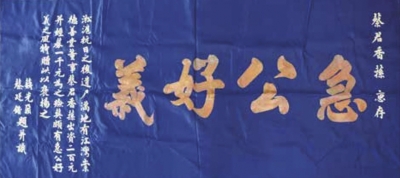■杨绣丽
路易·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0年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虹口消防队从事灭火、防火等工作。在虹口消防救援站队史馆内展出的众多老照片中,展出了路易·艾黎的一张人像照,身着军装,面目俊朗,略带温暖的目光,似乎正在表达着他和虹口消防以及中国的特殊情缘,表达着这个国际友人对中国进步未来的渴望!这种预见性的渴望可以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的描述中窥见一斑,在斯诺的印象里,艾黎“有极强健的四肢……两条巨腿阔步而行,他那蓝色、深邃的双眸中,仿佛可以看到远方地平线。”远方的地平线,红门正起航……
一、初登世界舞台
1922年3月,美国驻北京公使休门致函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邀请中国参加当年3月9日至18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万国消防联合会(出自《东方消防》杂志)。
当局颇感为难,时值军阀混战之际,北洋政府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根本没把消防工作排上议事日程。内务部虽然主管警政,但没有管理消防工作的官员,要派吧,哪里找得出“具有救火专门学问,堪充莅会之任”者。不派吧,堂堂中华竟派不出相应人员,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面上说不过去。最后政府决定,内务部不派官员参加,通知消防机构和设施比较完善一点的城市派人出席。
当时要论消防机构和设施之完善首推上海,只是上海的消防主要由英法在租界操办,不属北洋政府管辖。内务部又想到上海救火联合会,尽管该会不归官厅所属,完全民办,但装备较好。于是内务部发文通知江苏省淞沪警察厅,要他们同上海救火联合会迅即会商,遴选熟悉消防技术人员二、三员参会。
上海救火联合会作为民办义务消防组织,到1912年,已设置东、南、西、北四个区救火会,会员达359人,装备英法制造的泵浦车4辆,扶梯车4辆,胶带车4辆,在辖区内安装了800余只消火栓,成绩显著,在全国影响很大。
联合会最终决定选派朱良才和徐星斋参会,朱良才33岁,本是棉花商店的职员,时任沪南区救火会主任;徐星斋28岁,本为铁路技师,精通机械,时任沪北区江湾救火会队员,他们不仅热心公益、献身消防,而且谙熟英语。
也因此,中国第一次参与万国消防联合会,也留下了江湾消防队员的光辉记录。
由此是首次参加国际会议,不知道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带哪些文件资料,救火会随即于5月12日发函请教京师警察厅,请他们把万国消防联合会的通知和调查提纲,以及京师警察厅答复的原稿一并抄示,俾资借鉴。京师警察厅消防处收函后热情支持,满足上海的要求,于是救火联合会按万国消防联合会提出的15个问题逐条回答,作为与会的主要文件资料,这是反映上世纪20年代我国民办消防的重要史料。
两人的与会旅差费共需4400银元,救火联合会开始寄希望于北洋政府,可内务部接到报告迟迟没有下文。经一再催促,仍然拖到7月1日,淞沪警察厅才通知救火联合会,政府不解决旅费。
行期在迫,川资无着,好不急人!鉴于事关国际,救火联合会负责人毛经畴等不得不出面借银五千元,垫付朱、徐两人赴会费用。赴美参会的文件资料准备就绪,川资也借贷妥了,护照又成了难题,救火联合会派副会长穆湘瑶去北京四处奔走催办,等朱、徐两人拿到护照,已是启航前夕了。
朱徐两人代表中国参加万国消防联合会议,不仅是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大事,也是我国消防界的大事。隆重而热闹的欢送活动持续了4天,上海报界连续作了报道。7月8日,欢送活动进入高潮,救火联合会诸同人,会同专程来沪的江浙两省30多个县救火会的代表200余人,在救火联合会总部举行盛大的欢送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还有英法租界救火会的外籍消防人员,总共400余人。江浙两省救火会的代表在宴会上致了《颂词》,朱徐两人致了答词。
朱徐两人在答词中表示,诸君子联翩莅止,宠锡感筵,辞藻缤纷,足壮行色。会议终了,遄返乡邦,得幸不负地方父老者之众望,皆今日诸先生有以教之。
朱徐到旧金山时离开会日期还有一周,他们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如饥似渴地参观学习。旧金山市历史上发生过几乎全城毁灭的重大火灾,对消防工作极为重视,消防机构和设施相当完善。市消防总队长马肥亲自陪同,介绍情况。
朱徐回国后,上海救火联合会的领导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后,对消防工作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们一方面深感消防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深感我国的消防工作仍十分落后,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于是会长毛经畴、副会长莫锡纶、穆湘瑶联名,于1922年11月11日写了《呈江苏韩省长文》,慷慨陈词,劝办火政,为发展地方消防大声疾呼。
韩紫石省长对救火联合会的建议十分重视,于10月23日批示:“据呈已悉,候通会警察厅,县知事暨各警察局,一体查照,妥速办理,并随时据报察援”。同时将《呈江苏韩省长文》通会全省贯彻执行。旧中国许多热心消防的有志之士为发展我国的消防事业不遗余力。
尽管在反动统治的桎梏下,他们的许多设想在当时只是一纸空文,但他们的参会,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消防,带回了国外先进的消防技术和管理制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他们为成就消防事业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初识路易·艾黎
1927年4月21日,上海十六铺码头,30岁的路易·艾黎走下轮船,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座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陌生城市。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不用办任何手续,外国人可以随意在这个国家通行。
从码头往外走的时候,一个中国工人从他身边经过,鄙夷地盯了他一眼,然后吐了口唾沫。艾黎并没有发作,只是不明白工人为什么对他这样。因为我是外国人吗?他擦掉唾沫,快步离开了码头,他在大街上转着,最后住进了四川路的一家小客栈。
一路上,他发现在市区几条主要道路上,车水马龙,建筑高大宏伟,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在高大建筑的后面,却是迷宫一般的逼仄小巷,拥挤不堪的木质结构房子,臭气熏天,到处都可见乞丐……上海的这种贫富悬殊令艾黎感到吃惊。
在他的打算中,这或许算是一次不算长也不算短暂的旅行,他办的是为期6个月的签证。此时此刻,他绝对想象不到,他将愈来愈深地卷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直至成为20世纪上海消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易·艾黎曾作为新西兰远征军的一员开赴欧洲战场,经历过生死考验,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战后,这位老兵回国办起了牧场,每天要花上16小时砍灌木、架围栏、修公路、赶牲畜,还要自己种菜、挤奶、烧火做饭。由于战后新西兰经济形势恶化,他的生活十分艰苦。
1926年,就在牧场经营无以为继,不得不关闭的那一年,艾黎从报刊上读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消息。天生的好奇心再次被激发起来,他立马决定去中国。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上海后,他竟然穿起了一套比当年的战服还要沉重的消防装。
几经辗转,朋友曾告诉他巡捕房正在招募巡捕,他打过仗,应该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他似乎不感兴趣,却执意在工部局火政处找了一份消防员的工作。比起巡捕房,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薪水不算高,弄不好还要搭上性命。但他想到了弄堂里简陋的房子和人们对火灾毫无防范的种种陋习,更重要的是,这是被租界当局忽视的社会底层,一旦发生火灾,逃生渺茫,后果不堪。他执意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毫无保留地去帮助那些无力的人。
他去了虹口救火会,因为出色的工作,他很快被任命为小队长。后来他在自述中回忆最初的消防岁月时说,“我每天下午通常去工厂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干了10个月,我记得,第一次值班,就赶上了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火警钟声又响了,我再次套上衣服,顺着爬杆滑下,跃上蓄势待发的消防车……我外出救火时负责2号救火车,车上有10名救火员,他们都很好,我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他带领的这支救火队,出警快,效率高,极受好评。
但他不喜欢跟上司打交道,唯独喜欢检查工厂,因为这样可以深入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车间,直接接触工人。他曾经回忆说:“我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这样的工作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学普通话和上海话!”
1932年,消防处所在的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调任工厂安全督察长,专门负责检查租界内工厂的安全设施。这一新职位算是彻底发挥了艾黎的特长,也符合他的兴趣。然而,这项工作却让艾黎极其痛苦,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残忍的场景,最让艾黎感到痛苦的是童工们在“黑工厂”里的遭际。当时的许多童工不过八九岁,往往要工作12个小时。后面还有工头手执铁鞭来回走动,如果童工稍有差错,不是被鞭打,就是被用开水烫。
“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艾黎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路易·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0年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虹口消防队从事灭火、防火等工作,他的同事和朋友们越来越看不懂他了。一年半后,这个不吸烟不跳舞的艾黎竟然宣布,他要长期在中国待下去,不回新西兰了。他们不知道的是,艾黎在缫丝厂看到那些童工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让他深受刺激。和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接触后,他意识到,不彻底改变社会现状,就没有出路。他想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在虹口消防救援站队史馆内展出的众多老照片中,展出了路易·艾黎的一张人像照,身着军装,面目俊朗,略带温暖的目光,似乎正在表达着他和虹口消防和中国的特殊情缘,表达着他对这国度进步未来的渴望!
他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厚的期待,这或许可以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的描述中窥见一斑。
1929年,埃德加·斯诺在一次旅行中认识了艾黎,在斯诺的印象里,艾黎的“面孔被太阳晒得通红,头发乱蓬蓬地竖起”,“有极强健的四肢……两条巨腿阔步而行,他那蓝色、深邃的双眸中,仿佛可以看到远方地平线。”
三、红色情缘
对于路易·艾黎而言,在上海的这段消防生涯,是他在中国革命事业的“萌芽阶段”,他找到了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成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1932年末,路易·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后又由史沫特莱引荐,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大批中国进步人士。
之后艾黎参加了上海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当时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装在他家屋顶上。正如1968年宋庆龄在为艾黎作证明时写到的那样,“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在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产品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打击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2月,艾黎得知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即将奔赴延安的消息。仿佛一个漂泊的游子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一样,艾黎马上收拾行装,登上医疗队的车奔向着心中的圣地——延安……
在延安,他第一次遇见了毛泽东。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忽然走了进来,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和他交谈,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毛泽东询问了艾黎工合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在对他们的事业表示赞许的同时,毛泽东还鼓励艾黎坚持下去。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
随着工合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急需大量的技术员和指导员,于是艾黎开始尝试办学。为了纪念自己在上海认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艾黎就将学校命名为培黎学校。培黎学校最初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开设的,因为大多数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于是就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
时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邀请艾黎到酒泉相见,对艾黎创办培黎学校的业绩和对解放军西进的全力支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艾黎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依然认为,我能够尽力为新中国工作,只要有此需要,我就将留在中国。”
1977年12月2日,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在总结艾黎一生的贡献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地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时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黎在中国的工作和奋斗长达60年之久,成为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为遭受剥削的工人奔走呼喊,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为贫苦孩子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可谓一生倾情奉献中国。他终身未婚,却儿孙满堂。他在中国收养的子女,很多已经四世同堂。
直到去世,艾黎先生一直在中国居住、工作,他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他的在华生涯,被世人视为传奇,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而在上海的5年消防生涯,则是他中国事业的起步,他热爱中国、服务中国、奉献中国的人生道路,也给当代消防人留下了启迪和思考。